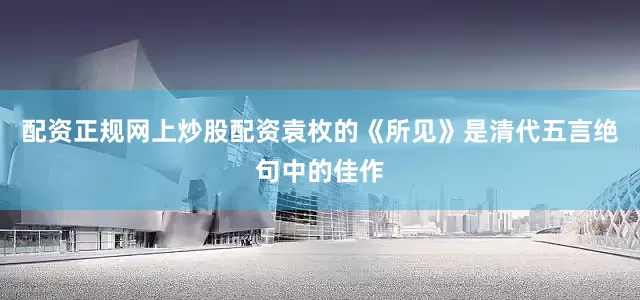#热问计划#
万历元年的北京城,刚当上首辅的张居正听到户部尚书王国光汇报国库状况时,脸都绿了。国库里只剩二十万两银子!这点钱连官员工资都发不出来。

更要命的是,前任首辅高拱临走前还吹牛说有四十万两。王国光冷笑:"那都是假账,把早就花掉的钱也算进去了。"
当时明朝的财政烂到什么程度?严嵩当权二十多年,贪了数百万两银子,家里光金银器皿就摆了几十桌。皇帝嘉靖也不是省油的灯,修道观炼丹一年花掉二三百万两。到了隆庆年间,户部尚书马森急得直跺脚:"太仓现存银仅够用三个月,京仓粮食只够两个月。"

话说得更绝:"就算神仙运输鬼帮忙,也没法解决这烂摊子。"

国库没钱,官员工资发不出,整个朝廷眼看要瘫痪。张居正想起韩信问路斩樵的故事。当年韩信投奔刘邦,走到秦岭发现栈道被烧,向樵夫问路后直接把人杀了。理由很简单:怕泄露行踪,成大事不能妇人之仁。
万历元年十一月,张居正推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政策:胡椒苏木折俸。说白了就是不发银子发香料,所有在京官员的工资都用胡椒和苏木抵。

这政策听起来荒唐,张居正却有自己的算盘。他告诉官员们:"这些香料价格昂贵,国家专营,民间买不到。现在用来抵工资,你们拿到手后很容易变现,收入只会高不会低。"

结果政策一出台就出事了。朝廷突然放出数万斤胡椒苏木,市场价格立马暴跌。官员们拿着香料到处找买家,根本卖不出去。
最惨的是礼部主事童立本。这人家境贫寒,全靠那点工资过日子。拿了胡椒苏木回家却变不了现,又拉不下脸去借钱,眼看家人要饿死,最后上吊自杀了。

童立本一死,朝野哗然。高拱的余党抓住机会大做文章,指责张居正政策失当,逼死清官。他们以为抓到了张居正的把柄,要借此把他搞下台。
这些人哪里知道,他们正中了张居正的圈套。

张居正府上的管家游七收到三十斤胡椒苏木后,立刻有好几波人上门想高价收购。游七开始还客气推辞,后来被张居正骂了一顿,才明白老爷的用意。

徐爵带着绸缎店老板郝一标来了。郝一标二话不说就用二百两银子买走那袋香料,比市价高了好几倍。临走还给了游七二百两银票做"孝敬"。
张居正知道后,不但没夸游七,反而又骂了一顿:"多拿一两银子都算受贿!赶紧退回去!"

可张居正心里明镜似的。郝一标这样的富商最喜欢攀附权贵,指望将来得到好处。京城里这样的人多得是,正好可以利用。

张居正把这些商人当成韩信故事里的"樵夫"。他要"问路"——让商人们告诉他如何解决胡椒苏木变现问题。然后就该"斩樵"了。
张居正找到郝一标,开门见山:"我知道你在很多官员那里收购胡椒苏木,既然有需要,不如直接跟朝廷做生意,价格公道。"

郝一标苦着脸也得答应。这段时间他已经花了一万多两收购各种官员的香料,就是为了讨好权贵。现在首辅开口,哪敢拒绝?

虽然张居正没给任何承诺,但郝一标觉得值。能抱上内阁首辅这条大腿,现在损失点银子算什么?将来随便给点生意都能赚回来。
就这样,张居正轻松解决了胡椒苏木变现问题。但这只是开胃菜,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。

童立本的葬礼那天,高拱的心腹王希烈组织一大批官员参加,想借机发动倒张运动。结果胡同里的祭品突然起火,火势凶猛,现场一片混乱。
这场"意外"火灾烧死了好几个官员,王希烈也在踩踏中丧命。朝野都知道不是巧合,但没人敢明说。

张居正事后以"非法聚会、引发火灾"为名,把参与闹事的官员(都是高拱亲信)全部贬出京城。一场可能推翻他的政治风暴就这样化解了。

其实这场火是冯保策划的,但张居正知道后不但没生气,反而默许了。在权力斗争中,有时候必须用些见不得光的手段。让人觉得你冷酷无情,总比被当软柿子好。
清除政敌后,张居正开始处理与冯保的关系。这个"笑面虎"太监既是重要盟友,也是危险伙伴。

明朝的制度是内阁票拟,司礼监批红。冯保掌握代皇帝批奏折的权力,是张居正推行改革的关键。张居正先后送给冯保名琴七张、夜明珠九颗、珍珠帘五副,还有金三万两、银二十万两。

有人质问张居正:"你不是反腐败吗?为什么重用贪官?"
张居正回答:"用一个贪官,换来惩治更多贪官的权力,这买卖不亏。"

这就是张居正的政治哲学:为了更大目标,可以在细节上妥协。

但张居正也不是一味迁就冯保。他在太后面前给冯保戴高帽,说他廉洁奉公,然后让人上奏要清查内廷财务。冯保虽然不愿意,但看张居正面子还是同意了。
这次清理收回了一万多件瓷器,节省了不少开支。更重要的是,张居正实现了皇室与外廷财政分开,限制了皇权,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成就。

稳定政局后,张居正开始推行万历新政。他的考成法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,六科监察六部,内阁监察六科,提高了行政效率。
一条鞭法更是影响深远。把过去按地、户、丁分别征收的赋役制度,改为按土地、人丁征收银两,简化了税制,增加了收入。

效果立竿见影。隆庆元年太仓银库只有23万两,万历五年猛增到435.94万两,十年间涨了近20倍。

军事上重用戚继光、李成梁等名将,水利上任用潘季驯治河,都取得显著成效。明朝出现了短暂的"万历中兴"。
张居正对成就很自豪:"万历以来,主圣时清,吏治廉勤,民生康阜,纪纲振肃,风俗朴淳。岭海之间,氛廓波恬;漠北骄虏,来享来王。一时海内,号称熙洽。"

有人批评张居正与太监往来,丧失了儒家知识分子的骨气。张居正回应:"古今大臣,侍君难,侍幼君更难。为了办成一件事情,你不得不呕心沥血,曲尽其巧。我想的是天下臣民,至于别人怎么看我,在所不计。"

这段话道出了张居正政治哲学的核心:为了国家和百姓利益,个人名声得失都可以不要。
张居正深知自己的做法在道德上有争议,但他认为这是实现更大目标的必要代价。与其说他是改革家,不如说是务实的政治家。

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:真正的政治家不是要做完美的好人,而是在复杂现实中找到实现目标的最有效路径。

正如后人评价:"功在社稷,过在身家。"张居正虽然个人操守有瑕疵,但对国家的贡献不可否认。
真正实盘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